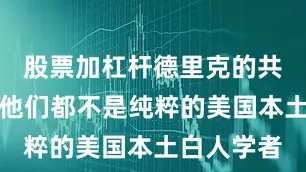
导读:当中美之间的教育比较、青年身份认同与文明对话成为当下跨文化交流的核心议题时,一位兼具中美学术视野、深耕美国高等教育一线的学者,其观察往往能打破刻板论述,触及差异背后的深层逻辑。
2025年3月,伍国教授在美国中世纪年会地点 哈佛大学Sever Hall 前留影
简介:伍国,四川乐至人,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教授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学生运动与文化变迁。他开设的课程涵盖从晚清以来的社会抗争与青年亚文化、东亚近代政治变迁、女性解放运动,到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革命与国家记忆重塑。他的教学强调跨文化理解与历史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致力于拓展学生对中国与全球现代性的比较视野。
采访人:朱泽睿,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赵逸轩、魏思雨、马子倩等对本采访亦有贡献)
01
展开剩余94%中美教育差异
学人:您在中国接受英语文学本科训练、在美国完成历史博士研究,这样的跨学科路径如何影响您对历史书写方式、国家叙事和现代性的理解?
伍国:应该是有影响的。事实上在受英美文学和系统的翻译训练之前,我比较深地受中国文学影响,在高中阶段读了很多现当代小说,也读李敖,龙应台等人的文化批判作品。对我个人来说,可能导致我比较喜欢研究历史中个人以及以个人为基础的小群体的命运和际遇。但我想指出,美国学界实际上也是非常注重这种研究的。最近出版的大卫蓝普顿的回忆录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 里边提到,他也对人物进行过传记性研究。当然, 现在的学术界要想立足,政治学圈子越来越看重社会科学性质的量化研究,统计和数学分析的应用,这样比较容易发表和受到认可,但是从真正认识社会的角度来说,对人的研究还是很重要的,而且美国对此其实非常重视。当然我只是后来发觉我的兴趣和这个有点重合,并不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西方文学作品对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心态非常重要。像我以前读的米尔顿长诗《失乐园》,戈尔丁小说《蝇王》,毛姆的短篇小说,埃米莉迪金森的诗等等,对个人认知和感悟都有很大价值。我最近重新读毛姆小说,发现他写到的很多内容,比如热带小岛上的英国人生活,与当地土著的互动,完全具有人类学意味。
从学术角度说,对个体的重视大概可以归为对人的能动性(agency)的强调,我可能偏向这方面。国家叙事,国家-社会关系,现代性,这些准确地说是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范畴内的概念框架,它们和文学没有多大直接关系,也谈不上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文学到历史,从历史到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递进的学习过程。但是也可以整合。比如,我在研究土改诉苦的一篇英文论文里,引用了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主要在结论部分,但在实证部分,还是落实在一个个具体人身上,比如,引用了谭其骧日记里他参加土改的记录。我想这就是对个体经验的重视。做社科研究,理论意识和理论力度还是非常重要的,但对我来说, 文学学习经验作为背景也很重要,事实上我尝试写过中文短篇小说,而且正式发表过,但从此我感觉从事虚构创意写作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小说家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自己很难做下去,因为我只是把一段真实的经历用看来小说的风格写了出来。我甚至觉得社会科学或者人文学科研究破坏了我可能有的想象力,让我永远在论证,在讲逻辑,在得出结论,所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美国社会学家会提出“ 社会学家的想象力”这个问题。
伍国老师任教课程的分组讨论
学人:您长期在美国文理学院任教,而美国的文理学院教育在理念与实践上,与综合性大学有显著不同。文理学院强调通识教育,自我发现与跨学科探索。而在中国,通识教育改革也正在逐步推进,但其路径,目标与实践逻辑或许并不相同。 您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通识教育”上的不同起点?在实践中,又各自面临怎样的现实挑战与制度局限?
伍国:我想指出,在美国引入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之前,美式高等教育的核心和最初的实践就是小型的自由文理教育,哈佛大学最初就是一个自由文理学院Harvard College 。在美国人的文化心理中,自由文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精髓,正因为它不是在培养专业化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学术精英(博士群体),而是培养普通美国公民中有担当意识的精英分子,而美国历史上很多总统都毕业于自由文理学院,很多著名学者也是在自由文理学院开始学术启蒙。
可以说,自由文理学院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味,这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通识” 或者“懂得多”,我必须澄清这一点: 自由文理教育不等于通识教育。比如,我们要对大一新生进行长达一个学期的当众口头演讲(public speaking)训练,这不是懂得多不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有效表达和交流, 说服听众的问题。 在学术训练一面,文理学院的小班制给学生很多自由讨论的机会,并从事大量的初步然而很专业的研究,而州立大学的“通识教育” 则一般是讲课+考试,因为学生人数实在太多了,无法组织讨论。我觉得这是美国传统精英教育中很重要,但被中国人忽视的一部分。
“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本身其实更多是在美国的州立大学和综合研究性大学的本科部分开展, 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具备基本的人文知识和素养。我比较熟悉的就是西方文明史和世界史课程,在州立大学,所有本科生都必须把世界史,西方文明史,和一些中国史亚洲史课程作为“通识”来上才能毕业,但并不需要特别深入。文理学院反而不用这个“通识教育”这个概念,比如我所在的学校和历史系,并不提供世界史和西方文明史(有些华裔学者说美国所有大学生都必须上西方文明史,这是不准确的),历史专业学生直接学习深度的国别史,研读原始资料,而且以写出毕业论文为最高目标和毕业要求,训练深度超过大型校园里“通识教育”中的历史课程。其他专业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也可以选上各种国别史,但我们并不叫通识教育,也不使用General Education这个术语,总的来说研究性更强,甚至可以说是“ 把对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放到本科生身上”——我认为这是对自由文理学院的准确理解。
中国高等教育有一个和美国完全不同的背景,就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苏式教育改革,建立了很多高度专业化的学院,如矿业学院,航空学院,钢铁学院,现在的通识教育是在纠正这种过度偏重理工科训练而忽视人文通识和审美情趣的缺陷。而美国,正如我刚才说的,哈佛从一开始就是强调广博的自由文理教育,普林斯顿大学始终抵制实用学科,所以不存在中国特有的问题。另外,所有美国老牌自由文理学院都有教会背景。我们学校经过多次辩论,在几年前决定彻底摆脱教会的影响,不再在毕业典礼上由学校牧师主持搞起立祷告。这对我也是一种解脱,因为我很讨厌那个祷告。就像我刚才讲的,美国的自由文理学院有大量的学生参与,观点分享,史料讨论,如果中国的通识教育也能这样,当然是好事,但这对教师组织和把控讨论的能力要求比较高。有效组织课堂讨论,随机回答问题,引导学生,肯定比自己连续讲课更据挑战性,因为你无法预测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或者关注哪个点。
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鲁迅小说
学人:您如何看待“线性历史”(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复线历史”之间的关系?在您的研究或教学中,如何向学生传达非西方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的可能性?这些理论(如历史终结论)在苏联解体后迎来其影响力的巅峰,成为西方世界理解国际秩序的核心范式之一。但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目前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中国的现代化与崛起并不与英美主导的国家历史叙事平行时,这些理论是否还具有它的有效性?以及美国学者是否还广泛支持这一历史终结论的观点?或者说,是否也在出现一种反思的趋势?
伍国:我曾和杜赞奇教授在2009年左右进行过一次面对面,一对一的交谈,是我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也交换了一些看法。我们也谈到了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福山(我可能是最早以中文评述福山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作者,书评见《读书》2011年第十二期)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会做出论断和预言,而提出复线历史的杜赞奇是历史学家,当然是历史学家里更具有理论意识的一位大家。历史学家一般避免做宏大预言,但是可能提出一种研究范式,我理解“复线历史” 就是后者。或者说,福山提出的是一种先知预言式的,带有独断性的“史观”,而杜赞奇提出的只是一种可供考虑的“历史学研究路径”。非西方的现代性,其实我一直在教学中向美国学生传达,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读一读已故的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关于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研究。我读书时在一次会议上和他有过交流,觉得他很有趣也很宽容。
美国大学生确实需要更多地了解“非西方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 ,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很容易生活在西方中心和美国中心的霸权话语体系中难以自拔,毕竟环境如此。如果我们不讲,他们很难反思。我认为德里克作为土耳其裔学者也同样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感觉有必要伸张“非西方现代性”,挑战西方中心和美国中心视角。但是作为学者,这种传达必须是严谨的,基于实证基础和理论论证,才能说服学生,让学生在学理上思考,而不是认为你在课堂上胡侃一通——-这是绝对要注意的。
就我的了解,近几年连福山自己都反思他的终结论了,所以他也主张从治理效能和质量的角度看待中国。 我没有持续深入研究,也许说得不对,感觉他从当初的独断立场已经退后了一部。美国学界其他人可能也会认为他把话说得太满太早吧。假如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我会说,“历史终结论” 恰恰犯了美国历史学界对历史“目的论”teleology 的忌讳,所以我不相信美国历史学者里有多少会信奉这个终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复线,替代性,去中心是当代史学研究必然追求的。
图书馆馆员Douglas Anderson指导我的学生运用相关数据库和软件进行研究
学人:在上一次的采访,您曾提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些作品在突破民族国家中心叙事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杜赞奇、李欧梵到今日的多声部史学,您认为这一研究传统如何回应今日的全球结构性危机?
伍国:我在我所在的历史系一直呼吁一件事:部分地废除以国家和地区为叙事单元的历史教学,以主题叠加国别的方式来重新组织课程。例如,为什么学生必须从相互割裂开来的美国历史,俄罗斯历史,拉丁美洲历史,中国历史中选课?而不是从“革命史”,“女性史”,“贸易史”,“军事史” 这样的类别中选课,看看不同社会如何应对同一历史课题? 为什么要诱导本来就有自我封闭倾向美国学生割裂世界历史的关联(interconnectedness)?现实中,这种分类就导致很多美国学生选择自己的舒适区,去学自己已经从小到大学了无数遍的美国史已求轻松毕业。现在我们确实逐步要朝我说的这个方向发展, 但这个过程很漫长。即使在美国,推动人们改变一个大家已经习惯多年的东西也是很困难的。
在您提到的“在突破民族国家中心叙事” “多声部史学” 方面,我想杜赞奇,李欧梵,德里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是纯粹的美国本土白人学者,甚至可以看成在英文学术语境中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 。他们对于多元叙事更为敏感,更愿意追求,因为如果你不是美国本土白人学者,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里百分之百会有某种疏离感(何炳棣,杜维明无不如此),而本地的白人学者往往没有这种动力去反思。这就是为什么, 我希望中国的年轻学子更注重这部分“第三世界” (或者全球南方吧)背景学者在文化碰撞和认同焦虑中产生的思想成果,而不是不加批评地去追捧一些经历简单,毕业于私立寄宿高中,从名校到名校,从名师到名师的白人学术精英的学术“成功之路”。我今天可以肯定地说, 作为母语不是英文的人文社科学者,我们在美国的挑战,焦虑,反思,哪怕人生感悟都比很多白人精英学者更复杂更深刻,也很难复制他们的成功,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独特性。
02
中美青年的未来
学人:人们的人格与世界观往往在10至20岁时形成。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时代美国社会传递出的集体价值与历史观?这会如何影响新一代美国青年的身份认同?
伍国:特朗普所代表的确实是一种极右翼民粹思潮,也标志着美国的全球战略正式开始收缩。其中,他刺激起来的排外情绪和对中国的仇视,在一些失意白人家庭那里会产生强大共鸣,我从一些思想保守的学生身上已经明显地看到了这个倾向。但是也并非所有学生都这样,有的美国学生也会产生逆反,政策上越是排外,年轻人越想了解真实的外界。这个也不奇怪,现在健在的很多美国汉学家都是在越战中成长的一代。在他们读博士的时候,美国政府越是妖魔化北越和“共产主义” ,他们越想了解真实的东亚,特别是中国。这在近期的一些访谈和回忆录中都有清晰的记载。
作为研究者和教学者,我仍然认为, 不论这个影响如何,我们可以尽可能发出理性的声音,也可以去影响他们,促进美国青年的深度思考。有一次我在一个微信群遇上几个华裔社科教授的辩论,主题是在教学中“影响”美国学生是需要做的吗?是做得到吗?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可欲性,第二是可行性。我个人的看法是:只要你表达,就是在影响他人,除非你什么都不说,所以这是无法逃避的。人文社科涉及的个人视角,背景,体验,价值观是不可否认的,而 华人教授和美国学生在年龄,阅历,背景方面有非常大的鸿沟,我觉得可以在专业性的基础上适当影响美国学生的世界观,让他们认识到世界的复杂和多元。在不同社会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比如美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有很多类似的焦虑,与父母的关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让美国学生感到美中之间既有很多共通的东西,可以共情的东西,又有不一样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我个人甚至不认为同龄的美国学生见识超过同龄的中国大学生,很多美国学生知识面和见识很小,但一旦帮助他们拓开格局,他们也会积极探索和思考。这不是影响是什么?
学人:同时,中国青年经历了一个快速崛起、政策频繁变动的十年,您如何理解他们所构建的“国家-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他们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想象?
伍国:我始终感到中国的年轻人中富于观察,富于思考的人非常之多,而且对外部世界有比美国青年更多的了解和学习的欲望,我和他们有过种种形式的交流和对话。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美国人家庭的生活水准是没有太大变化的,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明显的提高。这一代年轻人中很多人很早就出国,对美国肯定有更冷静甚至更批判的眼光,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自信。
我确实经历过华裔历史学界同行中老一辈学者的“不自信”,比如我们要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举办一个圆桌讨论,我觉得有了很好的题目,把观点自然地表达出来,然后交流答问就好(我自己在本校组织和主持过多学科圆桌讨论,效果很好),但似乎一些老一辈的华人学者就非常紧张,甚至有点害怕,甚至在内部反复强调“我们面对的是美国学者...” 云云然后反复演练,把气氛搞得很紧张,好像我们是一群参加国际比赛必须得奖不能出错的高中生,其实都是定居美国多年的中年学者, 用英文进行会议讨论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也证明我当时的预估没有错,因为我们讨论就是如何跨越师生之间的阅历和认知差异进行历史教学这个具有普世挑战的问题。在现场聆听的一位美国教授当场就说,有你们这样认真而且富于反思的华人教授,美国学生真是很幸运。经历了这个,我更觉得年轻一代更自信,更自如是应该的,这也是一种超越。
学人:在您看来,两国年轻人是被民族主义潮流推着走,还是有能力成为中美关系的“变量”?如何在教育和文化层面给予他们更多超越结构性叙事的“自我发现”空间?
伍国:我的回答就是 各自都更积极地看待对方,就比如美国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历史产生一种尊敬和理解,而中国学生也更多了解美国的进步历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正面意义上的“变量”。实际上中美两国一般民众对对方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媒体和各类出版物塑造的,这就是广义的“文化”,在狭义的“(学校)教育” 一面,这就是教师的职责,即引导学生建立一种共情能力,试图进行一种跨文化的理解,理解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并产生一种欣赏和共情。我后来在我的古代史课上彻底取消了闭卷考试,而以写总结,概述,研究论文为主,但其中我在期末设置了一个题目,就是一种假想的,其实没有固定答案的写作,就是:假定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愿意生活在哪一个朝代,为什么?或许这就是一种“自我发现”,一种穿越式的自我发现。而我自己则从中看出,美国学生会倾向于喜欢哪一个中国朝代,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卡特中心内关于中美关系的展览
03
对中西文化都秉持一份尊敬
学人: 您如何看待学者在今天中美关系中应扮演的角色?在对抗情绪蔓延的当下,历史学能如何重新赋予人们思考对方的能力?
伍国:学者应该尽可能准确地严肃地提供自己的分析。我已经注意到有的国内学者对海外华裔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海外华裔学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在地优势,提供对所在国的洞见和分析,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海外的华裔学者因为可以理解的乡愁,非常关注国内,有的美国华裔学者每天在微信群转发人人都能看见的国内公号发布的国内时事新闻,这些谁不知道呢?我觉得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对美国本身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多读一点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自身的东西,多出门旅行,走走看看,和美国人交流。
历史学的功用是毫无疑问的。我自己希望读到的有价值的东西要不就是具备某种理论维度,即对现象的理论提升,要不就是具有历史维度,在历史脉络中分析时事,如果纯粹进行时事快评,很多大学教授不如媒体甚至自媒体做得好,因为这不是学者的强项。
学人:当前,“吃尽时代黑利”似乎成了许多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流传的一种失落感。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还有身份认同,归属感缺失等多重挑战。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断裂与加速变化的时代,您想对这些身处夹缝中的年轻人说些什么?他们如何应该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中理解自己的位置,并找到前行的方向?
伍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时代确实变了。我在国内所完整经历的20世纪90年代和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样。我理解今天的失落,焦虑和不确定感,或者自认为很倒霉。但是我想说, 人类历史上即使在看来最无望最反智的时代,也有认真读书,认真思考的人,最终都需要有扎实的知识的人,有价值的思想最终都会留下来,或者被发现。实际上,在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即2001年开始,身边多数同学就都在学计算机信息系统。学化学的,学物理的也在转计算机,也常常有人问我什么时候转专业学计算机,可是我是个数学都不及格的人我也没办法,也没兴趣,我觉得历史很有趣教授也很好。我那时还勤工俭学打工读书,就是这样也没有放弃。当时留学的同学里有一个学物理的好友,后来海归在上海做物理学教授,从没想过换专业,自己享受专业兴趣就好了。说句开玩笑的话,你肯定不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现在这个时代的问题除了上面这些大环境挑战以外,还有各种媒体自媒体狂轰乱炸,信息过载,以及人工智能的兴起。所以我也问自己,如果学生在课堂上能学到的“历史知识”,通过ChatGPT 可以一秒找到还能步步深入,还能列表对比,还要我干什么?我的位置和方向又在哪里?所以我或许回答“年轻人”,也或许回答自己: 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过度消极,扎扎实实读书治学,对中西文化都秉持一份尊敬,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独特价值的人。
学人:最后,您希望怎样的青年能够成为真正的文明对话者?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如何培养出既有根性又能跨界的思维者?
伍国:也许是老生常谈,还是读书,读经过历史挑选积淀的经典,我还是主张 读一些中国古代经典。过去的现代化范式造成对中国古书有些偏见,但我到了中年反复重读一些包括汉代古诗,魏晋南北朝诗,《世说新语》,《古文观止》这些文本,确实能感觉那种情感和韵味,甚至幽默感,读赵翼的《廿二史史札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这些书,会感到中国古人那种批判意识,只是中国人的批判方式和现代西方有点不同。西方学者中以现代社科方法研究中国的学者,或者以历史档案为基础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我看来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们以为中国藏在档案里,其实完整的中国藏在各种文本里,包括唐诗宋词元曲。他们如果读一些中国文本,那也是作为资料,抱着明确的研究的功利目的去解读,而且时常没有读正确就没开始想当然地英译,就是说他终究是“外在”的,而 中国人则常常是在没有功利目的的状态下去品味母语文本,而且会反复地去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根性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是“内在”于我们的。所以回到文学话题,我倒确实觉得现代西方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八股,越来越没有情感,没有温度,貌似客观其实不乏预设立场,所以我们不妨借助文学回到人性和社会本真的一面。很多时候,虚构的故事写出了真实的人间,真实的数据却得出虚假的结论。不是吗?
因为视角和深度不同,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和中国人之间对中国的理解事实上是有隔阂的。比如,很多美国学者不理解为什么“新清史”在中国引起抵制;为什么王小波这个在当代中国有着巨大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标志性人物,在美国的译介,接受,和影响极其有限;为什么在英文世界,“汪晖”比“秦晖”的实际影响要大得多?在同样的文本中,双方各自看见的或者寻找的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精神上更多沉浸在中文文字世界中的人,你如何去跨界思维,认识到这种现实存在的隔阂,再去建立连接? 可能首先在于对两个“界”都要搞透一点,避免晚清改革者早就批评过的 “既不知西也不知中” 的弊病。这可能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沉潜下来独自阅读和思考,观察社会,然后才能在有机会的时候进行有意义的文明对话,而这个平台,可以是小众学术,也可以是大众传播。未来的青年应该尝试数字化时代的多种可能的传播模式。最后,我想分享刚刚看到的,余世存老师的一句话: “我们应该比前辈更能看清中国文化可能的贡献。”谢谢。
来源:學人Scholar
声明:推文基于更好更多传递信息之目的,不代表一读EDU观点和立场,如有疏漏及不足之处,请随时指正。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后台留言,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
好消息
如果您希望获取更多教育报告,请使用电脑复制以下链接至浏览器,注册登录"高教管理与研究平台",免费下载近300份教育报告、专家ppt(需使用电脑)
https://ai.squarestrategics.com/assistant-cn/prophet-library?_page=knowledge&source=1004A
发布于:北京市贝格富配资-配资平台有哪些-股票无息配资-配资官网app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